幸福街電視劇(幸福街電視劇情景喜劇)
當代書評丨平凡生活百姓家——讀何頓的長篇小說《幸福街》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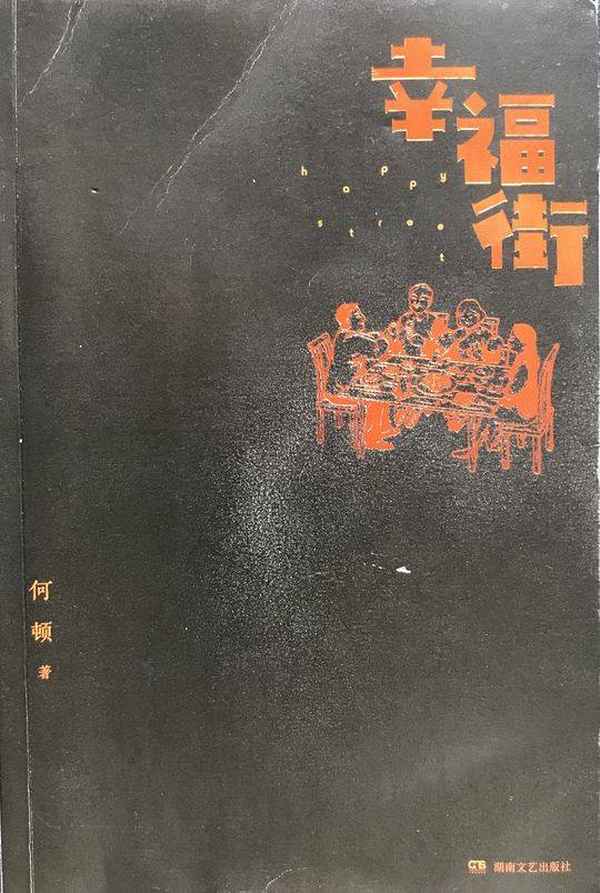
高海平/文
何頓是一位勤奮的作家,我早年讀過他很多小說。剛剛讀完他在病榻上寫就的長達38萬字的小說《幸福街》,感覺還是那么溫暖和親切。溫暖體現在寫的是普通生活,親切體現在寫的是尋常百姓。小說就像一幅《清明上河圖》,展示了一個叫幸福街的地方,在十年浩劫、上山下鄉、改革開放,一直到現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發展變遷史,描寫了生活在其中的各色人等不同的命運。幸福街上,生活著一批幸福或不幸福的人。他們的命運既是時代所決定的,同時又是自己所主宰的。每個人最終走出了各自不同的人生軌跡。
其實,《幸福街》描寫的是黃家鎮的故事,黃家鎮包括迎賓路、幸福街、光裕里、由義巷、芙蓉路、下河街等街巷,幸福街是主街道。這是一座千年古鎮。
小說寫到:“幸福街是一條居住著八十戶人家的小街,一條平整的青石板路,街兩旁大多是古舊的平房,房前屋后都栽著果樹。橘子樹、柚子樹和楊梅樹居多,也有枇杷樹、桃樹和梨樹”。還有一棵幾百年的大樟樹,它是幸福街的象征。
幸福街,原名叫呂家巷。一九五一年給街巷釘門牌時,將它改名為幸福街。幸福街一號,是幢平房,原來居住的人家姓呂,解放前擁有大片良田,且經營著大米廠和三家米鋪,劃階級成分時,定為地主兼資本家,被改造了。房子分給了不同的人,這些人包括何家、陳家、高家,還有黃家。何家是外來戶,何天民是游擊隊出身,任大米廠廠長,李詠梅是迎賓路小學的校長,兒子何勇。陳家男人原來是呂家的家丁兼轎夫,兒子陳兵。高家男人是呂家的管家,兒子高曉華。黃迎春和孫映山兩口子是“四野”南下的河北人,黃迎春是區長,孫映山是醫院院長,女兒黃琳。
幸福街八號住著周蘭,周蘭是小學老師,男人林志華是個理發師,女兒林阿亞。幸福街三十號是棟兩層樓的紅磚房,居住著漂亮女人趙春花,大米廠職工,丈夫陳正石,舊社會是個資本家,街上的異南春飲食店,以前叫異南春茶樓就是他家的。打成“右派”后,一蹶不振,死時,女兒陳漫秋才四歲。幸福街七十號住著楊老師,男人是竹器廠的廠長,老革命,兒子黃國進。
住在光裕里的黃國輝,父親殺豬的,母親是大米廠職工。住在由義巷的張小山,父親當過副區長,屬于干部子弟。還有楊瓊,跟何勇、黃國輝、林阿亞同學。故事從他們開始的。
黃家鎮,雖是一個鎮子,但是一個大社會,人員眾多,成分復雜,企業很多,織布廠、樂器廠、大米廠、竹器廠、陶瓷廠、糖果餅干廠等等,不同的人員在不同的廠子里工作,社會風氣井然有序。造反運動開始后,像陳兵這樣的底層人物當上了造反派的副總司令,開始在幸福街上耀武揚威。而顯赫一時的區長黃迎春、副區長張小山的父親卻被揪了起來,實施專政。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,每個家庭和人的思想也跟著發生變化。那是一個劣幣驅逐良幣的時代,黑白顛倒的時代。
上山下鄉開始了,毛主席一句話:知識青年到農村去,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,很有必要。高曉華、黃琳去了,何勇、林阿亞也去了。熱血青年們懷揣夢想,奔赴廣闊天地。高曉華是一個典型代表,他意志堅定,一心要實現自己的既定目標,團結了包括黃琳在內的一批知青辦小農場,還入了黨。然而,命運給他開了個玩笑,追求的一切不僅是一場空,由此還得了精神分裂癥,連自己的性命也搭進去了,成為一個時代既悲催又可嘆的人物。黃琳與高曉華恰恰相反,她喜歡高曉華的高蹈,曾經率領造反派前往韶山。后來,卻成了地地道道的享樂主義者。由造反派“魔頭”,墮落為破罐子破摔的生活迷失者。
幸福街上的兩大美女林阿亞、陳漫秋是作家重點塑造的藝術形象。高考恢復后,兩人都考進了大學離開了幸福街,在上海和長沙生活和工作。
林阿亞,早年吃盡了生活的苦頭。她的祖父曾是軍閥孫傳芳部隊的一名連長,淞滬會戰時是團長。當了逃兵后,攜夫人逃到黃家鎮,定居下來,生下了林志華。林志華娶了周蘭,生了林阿亞。造反運動開始后,因為奶奶私藏了一把,家庭遭遇了滅頂之災。陳兵帶人操了她的家,奶奶、父親和母親被抓。她一個人像只小貓瑟縮在家。母親周蘭從獄中出來,又被當權者、區革委會嚴副主任騷擾和霸占。父親慘死在獄中,何勇幫她去收尸。這一切遭遇其實都是嚴副主任為了達到長期霸占周蘭的邪惡目的,故意制造的。曲折跌宕的家族史,為林阿亞的成長做了必要的鋪墊。可以說,林阿亞的意志是被磨礪出來的。
陳漫秋,四歲時父親就去世,母親趙春花處處謹小慎微,低調做人做事,簡直低到了塵埃里。自己如此,也要求女兒如此。金子總是要發光的。陳漫秋的才華慢慢被認可。上大學,當作家,實現人生理想。陳漫秋的家庭背景是資本家,父輩、祖輩早年飛黃騰達,過著榮華富貴的生活。她雖然沒有趕上,但是精神中彰顯著那種氣質。母親的管教是她成才的有效手段。
黃國進,比陳漫秋小三歲,卻成了陳漫秋的丈夫。黃國進大學畢業后進學校,后來到了教育廳,最后當了市長,是幸福街走出的最高級別官員。他父親是老革命,他從小管教很嚴,何勇、黃國輝、張小山們習武練拳的時候,他在家里練毛筆字。小學時,黃國進的母親楊老師特別欣賞陳漫秋,限于陳漫秋的出身不好,楊老師從來沒有大張旗鼓地表揚過陳漫秋,總是在說完一大堆話之后,假裝不經意提及一下而已,這樣的行為讓趙春花極為不滿。想不到陰差陽錯,最終兩家卻成了親。黃國進、陳漫秋夫妻二人夫唱婦隨,琴瑟和鳴,日子過得順風順水,真真演繹了一出才子佳人的佳話,應了那句老話:“女大三抱金磚”。
林阿亞、黃國進和陳漫秋上大學離開幸福街后,他(她)們漸漸地淡出了作家的視野。小說重點在幸福街。一直生活在這里的何勇、張小山、黃國輝等成了著力描述的對象。
何勇,最富有正能量的藝術形象。父親是大米廠廠長,母親是迎賓路小學校長,有一個很好的家庭環境。從小就有正義感,同學打架他會出頭露面,朋友有事也會兩肋插刀。林阿亞父親冤死獄中,他陪林阿亞到監獄收尸。何勇和林阿亞本是天生一對,地配一雙。林阿亞考上大學離開幸福街后,何勇能正確看待他和林阿亞的關系,并且對今后的發展走勢有明確的認識。他曾埋怨過自己荒廢了學業,沒能考上大學,但是,沒有埋怨林阿亞的離開。這就是何勇成熟和大度的表現。他不自暴自棄,沉著冷靜。在公安戰線上兢兢業業工作。抓逃犯,立大功,當所長,不膨脹,大是大非面前,堅持原則,能正確處理好公與私、重與輕的關系。面對張小山、黃國輝這樣的發小,犯了法,也不講私情,秉公執法,實屬幸福街上成長起來的優秀人才。
張小山、楊瓊的性格發展多少出乎意料之外。張小山,出身干部家庭,從小上進心很強,小學時為了當班長,發奮學習,成績突飛猛進。也樂于助人,幫隔壁的鄭嬸嬸挑水。改革開放以后,隨著時代大潮風起云涌,勇敢地做了弄潮兒,不甘落伍,與時俱進,開歌舞廳賺了大錢。只是受到幾次挫折后,性格發生了變化,人生開始了轉折。這一轉就永遠的萬劫不復,實為遺憾。
楊瓊的人生更是悲催。小學當過班長,好多同學追求的對象。命運多舛,丈夫臥病在床,兒子上學,為了生計,只得為生。不過,她有一顆善良的心,不抱怨,不逃避,勇敢面對,更是讓人唏噓不已。
黃國輝的人生走向合乎常理。家庭環境和性格鑄就了其平庸一生,僅僅平庸也就罷了,一介莽夫,一身蠻力,做事不動腦子,出事是遲早的。
小說塑造了眾多的人物形象,除了上述之外,還有王進、劉興、二毛等小學另一個班的同學,也是幸福街上的主人。承包魚塘、造假酒,啥賺錢干啥。幸福街上負面人物的代表。
小說還塑造了嚴副主任、劉大鼻子等靠造反起家的人物。這是時代的胎記,他們的出現是歷史無法回避的必然選擇。
時光倏然,幸福街上的兩代人從這里出發,各行其道,最終各歸其所。也許這就是人生吧。
【如果您有新聞線索,歡迎向我們報料,一經采納有費用酬謝。報料微信關注:ihxdsb,報料QQ:3386405712】
專訪|小說《幸福街》作者何頓:“五零后”的“大江大河”
幸福街是一條住著八十戶人家的小街,平整的青石板路徐徐鋪開,街兩旁大多是古舊平房。街上幾個年齡相仿的孩子,都出生于1958年。他們的父母,有的是大米廠職工,有的是舊社會的資本家、姨太太,有的是小學老師,有的是政府干部,有的是理發師……這是小說中的幸福街,也是作家何頓曾真實生活過的幸福街。
何頓的父親曾是湖南第一師范學校校長,在“文革”中被打成“走資派”,一家人從學校宿舍區被趕出來,搬到了這個后來改名為“幸福街”的地方。在那個年代,幾家人共用廚房和廁所,打水要去自來水站,鄰里街坊抬頭低頭總能碰見,住一條街的孩子成天到晚玩在一起。
《幸福街》的主人公正是何頓兒時的玩伴們。這些孩子在此后的近半個世紀中經歷“文革”、上山下鄉、改革開放、恢復高考、“下海”大潮……命運與時代交疊,跌宕起伏,最終走向截然不同的結局。何頓把親身經歷和小說人物揉捏在一起,寫一代人的集體記憶,借主人公之口,反思了一代人的命運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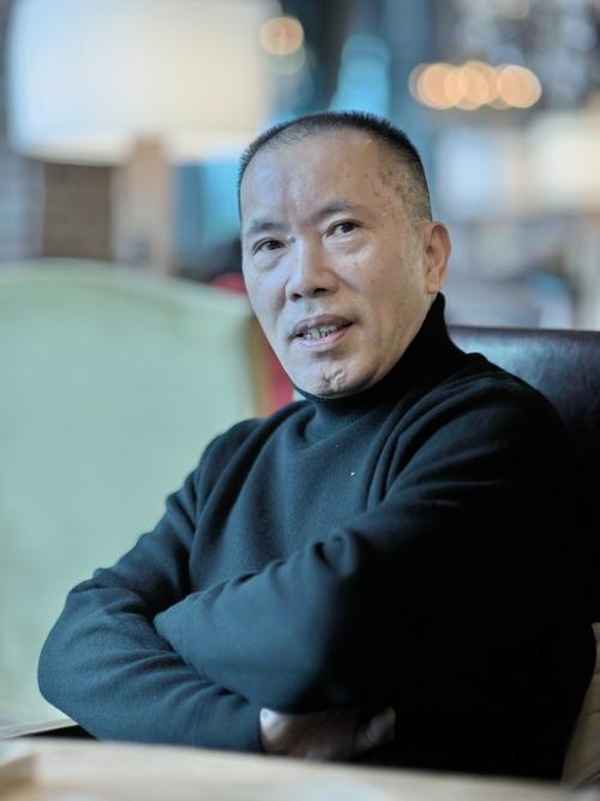
作家何頓,湖南省作家協會副主席
寫作時何頓正在一場大病中。手術前夜,他陷在對死亡恐懼與對生命思索的復雜情緒里,迷迷糊糊中,幾十年未曾聯系的兒時玩伴突然在夢里向他走來。他們為何在人最空虛的時刻閃現?他想,如果能活著走下手術臺,就要寫自己這代人的故事。
手術后第五天,何頓就開始了寫作。身世坎坷但要強上進的資本家女兒、無學可上的惶惑少年、沉迷三俠五義的叛逆青年、回不了城的女知青、下海經商的勞改釋放犯……他太熟悉了,那些形象幾乎是“自己跳進腦海里,再流到鍵盤上”。
2019年春節,小說里、也是現實中曾經在初中學校里排演革命樣板戲《沙家浜》的劇組在長沙重聚。當年的女同學,早已升級為奶奶和外婆。她們圍坐在一起讀剛剛出版的《幸福街》,小說主人公之一陳漫秋的原型也在。陳漫秋因為出身資本家家庭,前途于她只有孤獨和黯淡,但一番波折后進入學校劇組飾演正面人物阿慶嫂,是她初次為自己爭取來一絲光亮。她們給何頓發來的視頻中,當年飾演“沙奶奶”的同學輕聲讀出陳漫秋蹲在一隅讀劇本的片段。一段還沒讀完,女同學眼里都含著淚了。
《幸福街》,何頓著,湖南文藝出版社,2018年12月。
澎湃新聞:小說主人公均出生于1958年,跟您一樣大。您覺得這是怎樣的一代人?
何頓:我個人認為,我和我的哥哥姐姐那代人比起來,顯得更無知。
我在家排行第五,哥哥姐姐出生于1950年代初,他們在“文革”前接受過正規的小學和中學教育。即便在風聲最緊的時候,他們也會躲起來讀一些沒有封面的書,包括巴金的《家》、《青春之歌》等等,當時這些都是“禁書”。
我讀書時趕上政治運動,課本也改成了油印材料。我在小說中借主人公的口反思了當時“知識越多越反動”的想法,它確實對一些人造成了影響。
知青下鄉對我個人影響不大,因為我下鄉時已經是這場運動的尾聲,很快高考恢復,兩年不到我就考上了大學。但在我之前下鄉的知青,有些人被耽擱在那里許多年,就像小說里的桃桃和西西,她們的人生就被很大程度上改變了。
改革開放以后,市場經濟發展起來,有些工廠效益下降,一些小時候沒有好好接受教育、沒文化沒知識的人被迅速淘汰,有些人三十一二歲就下了崗。這時就出現了小說中黃國輝、張小山那樣的人,他們心思活絡、另謀出路,然而做事沒有底線,尤其在賺錢方面缺乏道德約束。
但并不是一個時代所有的人都不讀書。小說中的林阿亞、陳漫秋、黃國進,他們是自強不息、努力改變命運的人。1978年恢復高考,對于他們三人來說就是機遇。對我們這代人而言,考上大學、甚至考上中專,命運就徹底改變了,的確是知識改變命運。
不久前熱播的電視劇《大江大河》我也看了,我覺得很親切,很接地氣。里面的主人公和我小說中的人物年齡應該差不多,就是這代人的故事。
《大江大河》劇照
澎湃新聞:小說中兩個主要的女性人物林阿亞、陳漫秋,都是身世坎坷、但通過高考改變命運,這是一種理想的投射嗎?
何頓:她們都是真實的人物。那個年代的女孩比男孩聽話,愿意讀書,男孩貪玩。林阿亞、陳漫秋的“出身”不好,有些人被命運吞沒,有些人則是自強不息,林、陳都是后者,她們通過讀書改變了命運。
之前在一場講座上,有一位“90后”朋友向我提問,知識到底能不能改變命運?我想答案還是肯定的,我所經歷的歷史就是這樣的。
林阿亞就是我當年在生活中喜歡的一個女孩,乖巧聰明,她讀書就是因為好強、好勝。她出身在資本家的家庭,還是三姨太的女兒,在家里、在社會上都沒有地位,只能靠讀書來證明自己是個聰明女孩。寫她我是特別認真的,寫了好幾稿,生怕有任何輕慢、嘲諷的意思,生怕破壞了這個美好的形象。
澎湃新聞:您在小說里寫了很多具有年代感的細節,從喇叭褲、舞廳、到鄧麗君的流行,為什么花這么多筆墨?
何頓:我希望通過細節來讓讀者回想那個時代。每一個細節都經得起考證,因為那就是我的親身經歷。
喇叭褲,舞廳里的交誼舞,萬寶路的煙,就是八十年代在中國,至少是南方市場上興起的潮流,從香港、廣東、臺灣、福建這些沿海省份向湖南、江西這些內陸省份擴散。
我們一幫朋友開始跳舞的時候,就像小說里的張小山一樣,提著兩個喇叭的收音機,穿著喇叭褲和西裝,在長沙市的大街上跳舞。那還是1979年,剛剛改革開放,我們算是膽子很大的。有一種被壓抑了很久突然被釋放的感覺,人變得奔放、狂野。
澎湃新聞:剛才提到張小山這個人物,他心思活絡,租工廠的禮堂開舞廳,之后下海經商,一度風光無限,最后卻黯然收場,這是一個典型的時代故事嗎?
何頓:改革開放初期,社會氛圍剛剛有所松動,大部分有工作的人,比如我們這些進了工廠的,仍把希望寄托在單位上,或者還在觀望。而第一批出來做生意、開店的,不少是當時沒有正式工作的人員。
所以張小山這樣的人物出現是很正常的,因為他被單位除名了,他要活下去;后來追隨他的黃國輝,也是不得不從單位離開之后,才加入的。
八十年代末,張小山這樣的個體戶們開始騎摩托車、買大彩電,這對留在體制里的人是個巨大的刺激。
但九十年代以后,這批人就沒戲了,因為知識結構不行、知識準備不夠,做不大、做不好。相反,許多知識分子“下海”以后,經營得風生水起。到九十年代中后期,一大批當年做生意的人就進了麻將館,那已經不是他們的時代了。
這種淘汰非常殘酷,但也是很正常的。社會發展還是要靠知識和文化。張小山、黃國輝他們就是這種結果。
澎湃新聞:也有讀書的人物,比如高曉華,有雄心壯志,然而最后的命運也讓人唏噓。
何頓:高曉華的雄心是單純可笑的,他甚至想發明一種機器來消除人類腦中的自私自利,這是違反人性的。當社會氛圍改變之后,他覺得自己失寵了,陷入焦慮,還要寫信誣告別人。我想通過高曉華的命運,來預示一種荒誕的結束。
澎湃新聞:小說給許多人物都“安排”了閱讀史,比如說“出身”不好的陳漫秋說,是書給了她生活的勇氣,她讀《復活》《紅與黑》《基督山伯爵》,“書都翻爛了,封面也沒有了”,還要搭車去縣城新華書店,讀《悲慘世界》《浮士德》《獵人筆記》。如何設計每一個人物的精神資源,和您自身的閱讀經歷有關嗎?
何頓:陳漫秋讀的這些書,就是我的哥哥姐姐們當年悄悄讀的書。這就是那個年代的真實故事。
再比如,小說里的黃國輝是讀武俠小說,他崇尚肝膽相照的義氣,但最后也因盲目地“仗義”幫助犯法的朋友而葬送了自己。他在某種程度上是“文盲文化”的縮影。
我小時候是受哥哥姐姐的影響才讀了一點書。我父親是湖南第一師范的校長,家里還收藏了一些書。小時候對我影響比較大的是《水滸傳》。六七十年代宋江被批評為“投降主義”,當時以批判的形式出版了這部書,我父親就買回家來看。古典資源對我的影響比較深,但主要也不是從文學作品中來的,而是在茶館里聽人說書,聽老人家講故事,《說唐》、《水滸》這些。
澎湃新聞:您曾說小說中的何勇的原型就是自己。何勇和林阿亞因為其中一方考上大學而分開的結局,也是那個年代“知識改變命運”的注腳嗎?
何頓:何勇是個中規中矩的人,我是我們這代人中中規中矩的那一類。
何勇和林阿亞的結局是再普遍不過的,在我們那個年代,高考以后許多年輕人和戀人分手,尤其是像他們這樣,一個考去了大城市讀大學、一個留在小縣城,這是無可奈何的。
但何勇家早年曾幫助過林阿亞,幫她爭取上學、高考的機會,我生怕將林阿亞寫成一個忘恩負義的形象。如何駕馭這兩個人的故事,我左右搖擺了很久。我寫林阿亞1984年讀研究生時回到家鄉,仍然對何勇抱有希望,直到他看到何勇已經有了新的生活,才徹底放棄。這個故事也有原型,它是我們身邊一個女知青的真實經歷。
我想說的是,在這個故事里,沒有誰是壞人,它并非某一個人的責任。





